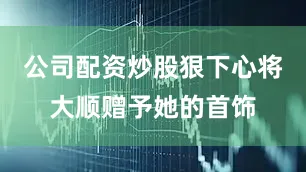王十月。
《作品》杂志创刊号。
最近一期《作品》杂志。
前不久,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成功举办。在文学周上,由广东省作协主办的《作品》杂志举办了一系列创刊70周年活动。其中,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分论坛“《作品》70年·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实践”研讨会上,由《作品》杂志走出来的素人作家尤为引人注目。这些素人作家让文学在新的时代,充满了活力和蓬勃的生命力。
展开剩余91%做保洁工作的王瑛在会上分享说:“看着自己发表的文字,我真的百感交集,热泪盈眶。”2024年8月,她完成了8万字的《擦亮高楼》投给了《作品》杂志,很快就得到了回复:“写得不错,真实感人。”《作品》2025年第1期,专门为她的这部非虚构作品开设了一个全新栏目“素人写作”,并以《清洁女工笔记》为题,刊发了这部作品。
近年来,《作品》杂志鼓励编辑“走出书斋,走向大众”,注重“平民化,亲和力”,坚持新大众文艺的文学探索与实践。在创刊70周年之际,更是将关注的目光与全部的深情与厚爱、光荣与梦想投向这些素人写作者。
今年是《作品》杂志创刊70周年,欧阳山、秦牧、萧殷等文坛大家曾历任《作品》主编,推出过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,如巴金的散文《怀念萧珊》、王蒙的小说《最宝贵的》、陈国凯的小说《我该怎么办》等。在上世纪80年代,更是引领“伤痕文学”的潮流。今天,《作品》不仅把素人作品,更是把素人作家带到聚光灯下,引领广东素人文学的潮流。
《作品》杂志是敏锐的,它一直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。70年来,这本杂志创造了怎样的“行走文学史”?这艘文学的“大船”将驶向何方?日前,南都记者独家专访了《作品》杂志社社长、知名作家王十月。
谈《作品》
始终保持参与社会变革的冲动
南都:《作品》创刊70年,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?
王十月:《作品》杂志社有一个陈列室,陈列着从1955年创刊至今的《作品》杂志,每次有朋友来,我都会带他们参观,每每也会引起观者的感慨。就像海子的诗中所写:“时间的重量……使石头开花。”如您所说,70年对一本文学杂志而言,意味着一部“行走的文学史”,但在我看来,它又不仅仅是一部“行走的文学史”,更是一部“行走的社会发展史”“行走的思想变迁史”。《作品》有一大特点,就是它从来不曾陷入鲁迅所说的“为文学而文学”,从1978年复刊后引领“伤痕文学”风潮,到上世纪90年代发“改革文学”、“打工文学”之先声;到今天,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践行一种平民文学观,我们一直在走自己的路,不为文学风潮所动。因此要问我最深的感触是什么,我觉得,《作品》这本杂志有着鲜明的近现代以来广东人开放、包容、务实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你看一两年、三五年的杂志不容易看出来,拉到70年的时间长度,就一目了然。
南都:70年的长卷中,最能代表《作品》精神的“高光时刻”是什么?为什么?
王十月:如果让我选,可能第一个高光点是1978年到1980年,这三年,《作品》有六部短篇小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,当时《作品》刊发王蒙先生《最宝贵的》,陈国凯先生《我该怎么办》等一大批作品,最早发出了思想解放的文学的声音。《作品》的前辈当年刊发这样一大批作品,不仅仅是他们对艺术的敏锐,也不仅仅是敢于担当的勇气,最难得的是思想的敏锐。这种意义和价值,我觉得可能到《作品》100年的时候会被看得更清楚。如果再选一个高光节点,我当然认为是2025年我们力推的一大批“素人写作者”引起了高度关注,成为大众讨论的话题。这件事的意义,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,也会慢慢凸显。
南都:70年,《作品》积累的最大财富是什么?《作品》的“灵魂”或“精神内核”是什么?是哪种不变的追求,让这本杂志历经风雨,依然挺立?
王十月:我认为《作品》最大的财富,就是70年来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参与社会变革的冲动。我们从来不曾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这种精神传承,如果往上追溯,要追溯到黄遵宪提倡的“诗界革命”、“我手写吾口”,追溯到梁启超倡导的“小说界革命”——强调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。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显得有些落伍或者保守,但《作品》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定力。《作品》一直是一本具有鲜明平民色彩的文学刊物,因此要问我《作品》的“灵魂”或“精神内核”是什么,我想就是这种“平民色彩”和参与社会变革的冲动。多年前,文学界就在呼吁作家要走出书斋、走向旷野,《作品》从来都不是一本囿于书斋的刊物。我想正是因为这种不变的追求,让我们历经风雨,走过低谷,但依然保持着自己最为核心的追求。
南都:《作品》杂志为广东乃至中国文学贡献了怎样独特的“作家谱系”?
王十月:广东当代文学史上大多数重要作家的成长,都与《作品》息息相关,当代最重要的中国作家几乎都在《作品》发表过重要的作品。但要说《作品》最独特的“作家谱系”,可能不是当下那些大热门的作家,而是从陈残云、王杏元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岭南农村生活的书写,到陈国凯、吕雷等的“改革文学”“都市文学”,再到后来的“打工文学”。这一谱系的一大特点,就是贴近时代,贴近生活,带有毛茸茸的生活质感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也就特别能理解,为什么《作品》一直力推“素人写作”了。
南都:作为扎根广东的文学杂志,《作品》如何体现岭南文化特色,并参与构建“岭南文学新气象”?
王十月:《作品》杂志一直重视对脚下这片大地的书写,1978年之前的《作品》发表了大量描写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,南方的丛林、河流、海风、椰林,割胶工、疍家渔民,组成了早期《作品》的鲜明特色。我们的创刊号,封面就是一片椰林。到了1978年之后,《作品》关注的重点,开始投向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广东,关注经济浪潮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。“改革文学”“都市文学”“打工文学”成为重点。下海,打工,特区等成为高频词。近年来,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做广东历史文化的梳理与书写,我们邀请著名作家先后开设了“珠江钩沉”“左迁录”“文化岭南”“广东左翼作家人物志”等专栏,对广东的历史文化进行多角度的深度书写,产生了较好的影响。我们不仅直面现实,梳理历史,也积极面向未来,我们是国内文学期刊中较早开设“科幻文学”专栏,倡导“未来现实主义”的文学期刊。我想,这就是我们参与构建“岭南文学新气象”的具体努力。
南都:像《作品》这样的文学期刊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?
王十月: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新型编辑人才奇缺。现在的编辑,不能只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从来稿中选稿、编稿的编辑。现在的编辑要求有更全面的能力,是从选题策划、组稿、编辑到新媒体传播全链条跟进的复合型人才。
南都:我看百度介绍:《作品》杂志在国内纯文学期刊中以高稿费著称,最高可达千字1500元。诗歌栏目的稿费标准为25元一行,是行业内的一线标准。这个稿费标准实行了多少年?现在还是这样吗?为什么?
王十月:这个信息并不准确,截至目前,我们的稿费在国内文学期刊中属于第二梯队的中间层,我们平均稿费只有千字600元,不过我们在稿费有限的条件下进行了一些创新,所有来稿均为千字500元,然后由读者参与投票评出季度和年度优秀作品,给予千字100至500元不等的二次和三次稿费。因此,理论上,每年会有极少量作品拿到千字1500元的稿费,从而造就了最高稿费1500元的口碑。明年,我们可能会像《花城》杂志一样提高稿酬标准,向国内一线稿酬标准看齐。
南都:全国这种200页以上的大型期刊定价还是20块的只有两家,一个是《作品》,另外一个是《江南》。《江南》杂志主编哲贵说看这定价,有点辛酸,他们准备提价了。你也会辛酸吗?你们也会提价吗?你怎么看这事?
王十月:我不觉得辛酸,也不准备提价。甚至每年征订季,我们还会优惠到15元一本。我们是一本平民化的刊物,我们的订户中,很多都是基层文学爱好者,我认为保持现在这样一个亲民的价格挺好。当然,这是基于我们杂志的现状做出的定价策略。
南都:纯文学对于普通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杂志未来有什么规划去应对新时代的阅读变化?
王十月:其实我们并不太认可“纯文学”这个概念,我们倡导以“严肃文学”取而代之。我们认为,优秀的严肃文学对普通人而言,意味着我们获得了和另外一个丰满灵魂交流的机会,当我们和越来越多的丰满的灵魂深度交流,我们的灵魂也会告别简单,走向丰满。明年杂志会做一些调整,但具体的改版方案,要等节后开编辑会定。初步想法,保留“素人写作”等优势栏目,会对栏目做一些整合,加强批评家的参与,但不想做成作品论或作家论,而是话题性的深度思考和书写。同时,还会加大视频号的经营力度。此外,也考虑做一档谈话类的新媒体节目,将杂志内容与新媒体进行更深度的融合。
谈素人写作
13年了,文学素人与文学界的“壁橱”还在
南都:你们杂志培养了很多新人,为什么会培养这些新人?选稿标准是什么?
王十月:其实也谈不上是我们培养了新人,杂志的任务,是按自己的标准,将一期期杂志的内容做好,而这些新人的作品,为我们杂志提供了新鲜的生活体验和新鲜的文本,因此也可以说,是他们成全了《作品》。我们选择的新人,一定是能为我们杂志增添光彩的人。我们选稿的标准是不求完美,苛求特别。我们更看重新人的潜力和可能性。我经常和编辑讲,木桶理论说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一只木桶装多少水,但我们选稿看的不是短板而是长板,每块板都很齐、但没有长板、四平八稳的作者不会被我们选中,我们要的是长板特别突出的作者,或者是他的生活,或者是他的语言,或者是他的思想,或者是他在文体上的探索,或是他塑造的人物……总之有一样是特出众的。至于他们的短板,在未来的写作中,他们会慢慢补齐,但那种没有长板的写作者,在未来的写作中,可能永远都不会长出长板。
南都:你怎么看素人写作?或者说新时代的大众文艺?
王十月:我们开设“素人写作”栏目,很多人疑惑,说什么样的人算素人?是一篇文章没有发过,还是发过十万字、二十万字的作品?事实上,在我的观念里,“素人写作”从来不是一个指向写作者身份的概念。如果说“素人写作”指向身份,那莫言、余华早期都是“素人写作”,所有的作家都是“素人写作”。我准备写篇文章,叫《作为一种美学思想的“素人写作”》。
在我看来,“素人写作”是一种美学思想,这种美学思想最本质的特点是“抱朴见素”,说通俗一点,就是用朴素的语言与形式,书写最本真的生命体验。大美不雕,在我的美学思想中,“素人写作”相对应的是“纯文学”。“纯文学”是为文学的文学,而“素人写作”是为人生的文学。
南都:“从农民到打工仔,再到专业作家,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完成了身份的蝶变”,还有“打工文学代表作家”,在你的词条上,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介绍。你自身也是素人写作转型的成功例子,对于这些新手作者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?
王十月:正是因为这种感同身受,使得我特别能读懂他们。而且不是那种因为“新大众文艺”热,于是表现出认同,我是打心眼里认同。事实上,我从做编辑开始,就一直在力推“素人写作”,只是今年才被更广泛关注到而已。
南都:相比当年,素人写作的成长空间有了什么样的变化?
王十月:我在《文艺报》发表过一篇谈东莞“素人写作”的文章,《从“他乡”到“我城”:东莞文学的精神流变》,从“他乡”到“我城”,就是我观察到的最本质的变化。现在的写作者对城市的认同,对他乡的认同,不再像我们过去那样,我们对城市没有认同感,很长一段时间,我是随时准备回农村。那时很多的打工者,出来打工,都是想着挣点钱,回家盖栋像样的房子。
南都: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提出要填平文学素人与文学界的鸿沟。你怎么看?应如何填平?
王十月:鸿沟的填平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这种鸿沟是怎么造成的呢?是我们的傲慢与偏见,我们认为文学应该是高雅的、体面的、是精英化的。而你们这些写作者,你们不够体面,不够高雅,你们的写作缺少“文学性”。2013年,李敬泽先生在东莞打工文学论坛演讲,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,我想摘录在这里,“文学,从本质上说,和高雅体面没多大关系。文学和诚恳忠直有关系,和人的眼泪、痛苦有关系,和人在梦想和困境中的奋斗以及人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有关系,这一切不一定是高雅的、不一定是体面的。一个人在疼痛的时候体面吗?一个人锥心刺骨地哭泣时高雅吗?所谓文学性,根本的前提是众生平等,尽可能忠直地容纳广博的人类经验。”这篇演讲稿后来以《“打工文学”与“壁橱”》为题发表,收在他的演讲集《空山横》中。
敬泽先生说的“壁橱”,就是谢有顺所说的鸿沟。13年过去了,“壁橱”还在。有作家和我聊到谢有顺的这个演讲很是感慨,我回复了一句话:“每个人都在带着自己的偏见看世界,一个人的智慧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打破偏见的能力。”我和《作品》所做的很多事,事实上,就是在为打破这种偏见而努力,也就是在为填平这鸿沟而努力。我想,只要我们坚持不懈,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打破偏见,能更客观地不带偏见地看待生活,看待文学。
谈个人
我的人生,有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做编辑
南都:你身兼著名作家和核心文学期刊社长双重身份,这种角色转换给你带来的最大挑战和乐趣是什么?
王十月:事实上,我已经做了23年编辑。也就是说,我的人生,有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做编辑。这个时间,和我写作的时长几乎高度重叠。我1999年开始写小说,2000年开始当编辑,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角色转换。当然,当编辑和当社长主编还是不一样的,社长主编有更多的自由在这本杂志上践行我对文学的理解。
最大的挑战,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,俗话说慈不掌兵,我给外界的印象是个很强悍的人,但我的强悍,更多是面对强者,对同事和弱者,我是个心特别软的人。这样的人带团队会比较累。好在同事们大多数时候都很自觉,大家对杂志和我的理念有认同感,没有将工作仅仅当成工作,而是当成了一份事业在做。很多到过《作品》杂志的作家朋友都说,《作品》的团队有一股子激情,这个很难得。当然还有一个挑战,就是我提出“内容经典化,传播大众化”的办刊理念,“传播大众化”难免会让人觉得这个主编不稳重,爱出风头。因此,网上骂我的人挺多,好在我内心比较强大。最大的乐趣,或者说最开心的事,是听到有人表扬《作品》杂志,当然也包括表扬作为社长主编的我。
南都:你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?
王十月:去年出版了长篇《不舍昼夜》。目前在写新的作品,但什么时候写出来,写得是否满意,都还是未知,计划赶不上变化,还是等写出来后再说。
南都:近年来,非虚构写作、AI生成内容、短视频解读文学等成为热点。您如何看待这些新现象对传统文学创作和阅读方式的冲击?
王十月:非虚构写作的兴起,事实上代表了读者对虚构类写作的不满,也代表了虚构类写作在处理当下复杂的生活经验时的无能。我用AI创作过几个短小说,发在微信公众号上,阅读量挺大。我认为AI作为一种工具,将来被写作者大量应用是肯定的。但我认为,如果我们使用了AI作为辅助,还是要明确标注“AI辅助创作”为宜。《作品》在发稿之前会做两件事,一是查抄、查重,二是查AI使用率,查出疑似AI创作占有一定比例但作者没有标注的稿件,我们会退稿。文学一直受科技发展的影响,活字印刷出现,才出现大部头的小说;互联网的兴起,才出现动辄上千万字的网络文学。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,未来的文学会受到怎样的影响,现在预测是不可靠的。但可以说,肯定是会受影响。
本版采写:南都记者 许晓蕾
发布于:广东省倍享策略-炒股怎么配资-配资app下载-股票如何加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证券目前正接受徐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
- 下一篇:没有了